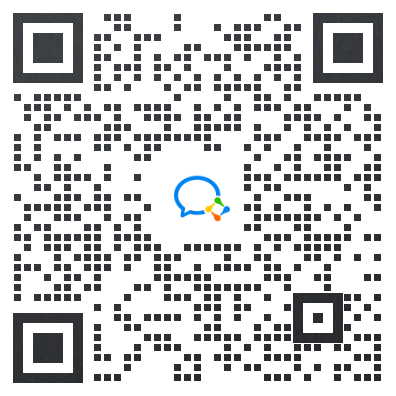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离婚时被误解的常识-解放军文职人员招聘-军队文职考试-红师教育
发布时间:2017-06-27 12:01:2712、青春损失赔偿误区有的女性婚姻当事人认为,在离婚时男方应当给予一定的青春损失赔偿。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婚损害赔偿只有在家庭暴力,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况下法院才能判决过错方给予赔偿。13、我不同意离就别想离有的当事人误认为只要自己坚持不同意离婚就不会判决离婚。事实上,如果有充分证据证明感情已经破裂,即使不同意离婚法院也会判决离婚。14、小孩抚养误区有的婚姻当事人误以为判决离婚后,小孩由另一方直接抚养,自己就没有任何义务了。实际上离婚解除的是婚姻关系,子女与父母的关系无法解除,双方还存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比如监护抚养赡养继承等。不直接抚养小孩的一方仍应当承担抚养费。
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离婚-解放军文职人员招聘-军队文职考试-红师教育
发布时间:2017-06-19 15:52:33离婚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你总以为他的父亲也得管他叫大哥,他的 大哥 味儿就这么足。张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作媒人和反对离婚。在他的眼中,凡为姑娘者必有个相当的丈夫,凡为小伙子者必有个合适的夫人。这相当的人物都在哪里呢?张大哥的全身整个儿是显微镜兼天平。在显微镜下发现了一位姑娘,脸上有几个麻子;他立刻就会在人海之中找到一位男人,说话有点结巴,或是眼睛有点近视。在天平上,麻子与近视眼恰好两相抵销,上等婚姻。近视眼容易忽略了麻子,而麻小姐当然不肯催促丈夫去配眼镜,马上进行双方 假如有必要 交换像片,只许成功,不准失败。自然张大哥的天平不能就这么简单。年龄,长像,家道,性格,八字,也都须细细测量过的;终身大事岂可马马虎虎!因此,亲友间有不经张大哥为媒而结婚者,他只派张大嫂去道喜,他自己决不去参观婚礼 看着伤心。这决不是出于嫉妒,而是善意的觉得这样的结婚,即使过得去,也不是上等婚姻;在张大哥的天平上是没有半点将就凑合的。离婚,据张大哥看,没有别的原因,完全因为媒人的天平不准。经他介绍而成家的还没有一个闹过离婚的,连提过这个意思的也没有。小两口打架吵嘴什么的是另一回事。一夜夫妻百日恩,不打不爱,抓破了鼻子打青了眼,和离婚还差着一万多里地,远得很呢。至于自由结婚,哼,和离婚是一件事的两端 根本没有上过天平。这类的喜事,连张大嫂也不去致贺,只派人去送一对喜联 虽然写的与挽联不同,也差不很多。介绍婚姻是创造,消灭离婚是艺术批评。张大哥虽然没这么明说,可是确有这番意思。媒人的天平不准是离婚的主因,所以打算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必须从新用他的天平估量一回,细细加以分析,然后设法把双方重量不等之处加上些砝码,便能一天云雾散,没事一大堆,家庭免于离散,律师只得干瞪眼 张大哥的朋友中没有挂律师牌子的。只有创造家配批评艺术,只有真正的媒人会消灭离婚。张大哥往往是打倒原来的媒人,进而为要到法厅去的夫妇的调停者;及至言归于好之后,夫妻便否认第一次的介绍人,而以张大哥为地道的大媒,一辈子感谢不尽。这样,他由批评者的地位仍回到创造家的宝座上去。大叔和大哥最适宜作媒人。张大哥与媒人是同一意义。 张大哥来了, 这一声出去,无论在哪个家庭里,姑娘们便红着脸躲到僻静地方去听自己的心跳。没儿没女的家庭 除了有丧事 见不着他的足迹。他来过一次,而在十天之内没有再来,那一家里必会有一半个枕头被哭湿了的。他的势力是操纵着人们的心灵。就是家中有四五十岁老姑娘的也欢迎他来,即使婚事无望,可是每来一次,总有人把已发灰的生命略加上些玫瑰色儿。张大哥是个博学的人,自幼便出经入史,似乎也读过《结婚的爱》。他必须读书,好证明自己的意见怎样妥当。他长着一对阴阳眼:左眼的上皮特别长,永远把眼珠囚禁着一半;右眼没有特色,一向是照常办公。这只左眼便是极细密的小筛子。右眼所读所见的一切,都要经过这半闭的左目筛过一番 那被囚禁的半个眼珠是向内看着自己的心的。这样;无论读什么,他自己的意见总是最妥善的;那与他意见不合之处,已随时被左眼给筛下去了。这个小筛子是天赐的珍宝。张大哥只对天生来的优越有点骄傲,此外他是谦卑和蔼的化身。凡事经小筛子一筛,永不会走到极端上去;走极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头的。张大哥最不喜欢摔跟头。他的衣裳,帽子,手套,烟斗,手杖,全是摩登人用过半年多,而顽固老还要再思索三两个月才敢用的时候的样式与风格。就好比一座社会的骆驼桥,张大哥的服装打扮是叫车马行人一看便放慢些脚步,可又不是完全停住不走。听张大哥的,没错! 凡是张家亲友要办喜事的少有不这么说的。彩汽车里另放一座小轿,是张大哥的发明。用彩汽车迎娶,已是公认为可以行得通的事。不过,大姑娘一辈子没坐过花轿,大小是个缺点。况且坐汽车须在门外下车,闲杂人等不干不净的都等着看新人,也不合体统,还不提什么吉祥不吉祥。汽车里另放小轿,没有再好的办法,张大哥的主意。汽车到了门口,拍,四个人搬出一顶轿屉!闲杂人等只有干瞪眼;除非自己去结婚,无从看见新娘子的面目。这顺手就是一种爱的教育,一种暗示。只有一次,在夏天,新娘子是由轿屉倒出来的,因为已经热昏过去。所以现在就是在秋天,彩汽车上顶总备好两个电扇,还是张大哥的发明;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假如人人有个满意的妻子,世界上决不会闹 共产 。张大哥深信此理。革命青年一结婚,便会老实起来,是个事实,张大哥于此点颇有证据。因此,在他的眼中,凡是未婚的人脸上起了几个小红点,或是已婚的眉头不大舒展,必定与婚事有关,而马上应当设法解决。不然,非出事不可!最远的旅行,他出过永定门。可是他晓得九江出磁,苏杭出绸缎,青岛是在山东,而山东人都在北平开猪肉铺。他没看见过海,也不希望看。世界的中心是北平。所以老李是乡下人,因为他不是生在北平。张大哥对乡下人特别表同情;有意离婚的多数是乡下人,乡间的媒人,正如山村里的医生,是不会十分高明的。生在乡下多少是个不幸。他们二位都在财政所作事。老李的学问与资格,凭良心说,都比张大哥强。可是他们坐在一处,张大哥若是象个伟人,老李还够不上个小书记员。张大哥要是和各国公使坐在一块儿谈心,一定会说出极动人的言语,而老李见着个女招待便手足无措。老李是光绪末年那拨子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孩子们中的一位。说不上来为什么那样不起眼。张大哥在没剪去发辫的时候,看着几乎象张勋那么有福气;剪发以后,头上稍微抹了点生发油,至不济象个银行经理。老李,在另一方面,穿上最新式的西服会在身上打转,好象里面絮着二斤滚成蛋的碎棉花。刚刮净的脸,会仿佛顺着刀子冒槐子水,又涩又暗。他递给人家带官衔的 财政所第二科科员 名片,人家似乎得思索半天,才敢承认这是事实。他要是说他学过银行和经济学,人家便更注意他的脸,好象他脸上有什么对不起银行和经济学的地方。其实老李并不丑;细高身量,宽眉大眼,嘴稍过大一些,一嘴整齐白健的牙。但是,他不顺眼。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下,他使人觉得不舒服。他自己似乎也知道这个,所以事事特别小心,结果是更显着慌张。人家要是给他倒上茶来,他必定要立起来,双手去接,好象只为洒人家一身茶,而且烫了自己的手。赶紧掏出手绢给人家擦抹,好顺手碰人家鼻子一下。然后,他一语不发,直到憋急了,抓起帽子就走,一气不定跑到哪里去。作起事来,他可是非常的细心。因此受累是他的事;见上司,出外差,分私钱,升官,一概没有他的份儿。公事以外,买书看书是他的娱乐。偶尔也独自去看一回电影。不过,设若前面或旁边有对摩登男女在黑影中偷偷的接个吻,他能浑身一麻,站起就走,皮鞋的铁掌专找女人的脚尖踩。至于张大哥呢,长长的脸,并不驴脸瓜搭,笑意常把脸往扁处纵上些,而且颇有些四五十岁的人当有的肉。高鼻子,阴阳眼,大耳唇,无论在哪儿也是个富泰的人。打扮得也体面:藏青哔叽袍,花驼绒里,青素缎坎肩,襟前有个小袋,插着金夹子自来水笔,向来没沾过墨水;有时候拿出来,用白绸子手绢擦擦钢笔尖。提着潍县漆的金箍手杖,杖尖永没挨过地。抽着英国银里烟斗,一边吸一边用珐蓝的洋火盒轻轻往下按烟叶。左手的四指上戴着金戒指,上刻着篆字姓名。袍子里面不穿小褂,而是一件西装的汗衫,因为最喜欢汗衫袖口那对镶着假宝石的袖扣。张大嫂给汗衫上钉上四个口袋,于是钱包,图章盒 永远不能离身,好随时往婚书上盖章 金表,全有了安放的地方,而且不易被小绺给扒了去。放假的日子,肩上有时候带着个小照像匣,可是至今还没开始照像。没有张大哥不爱的东西,特别是灵巧的小玩艺。中原公司,商务印书馆,吴彩霞南绣店,亨得利钟表行等的大减价日期,他比谁也记得准确。可是,他不买外国货。不买外货便是尽了一切爱国的责任;谁骂卖国贼,张大哥总有参加一齐骂的资格。他的经验是与日用百科全书有同样性质的。哪一界的事情,他都知道。哪一部的小官,他都作过。哪一党的职员,他都认识;可是永不关心党里的宗旨与主义。无论社会有什么样的变动,他老有事作;而且一进到个机关里,马上成为最得人的张大哥。新同事只须提起一个人,不论是科长,司长,还是书记员,他便闭死了左眼,用右眼笑着看烟斗的蓝烟,诚意的听着。等人家说完,他睁开左眼,低声的说: 他呀,我给他作过媒。 从此,全机关的人开始知道了来了位活神仙,月下老人的转身。从此,张大哥是一边办公,一边办婚事:多数的日子是没公事可办,而没有一天缺乏婚事的设计与经营。而且婚事越忙,就是公事也不必张大哥去办。 以婚治国, 他最忙的时候才这么说。给他来的电话比谁的也多,而工友并不讨厌他。特别是青年工友,只要伺候好了张科员大哥,准可以娶上个老婆,也许丑一点,可是两个箱子,四个匣子的陪送,早就在媒人的天平上放好。张大哥这程子精神特别好,因为同事的老李 有意 离婚。老李,晚上到家里吃个便饭。 张大哥请客无须问人家有工夫没有,而是干脆的命令着;可是命令得那么亲热,使你觉得就是有天大的事也得说有工夫。老李在什么也没说之中答应了。或者该说张大哥没等老李回答而替他答应了。等着老李回答一个问题是需要时间的:只要有人问他一件事,无论什么事,他就好象电话局司机生同时接到了好几个要码的,非等到逐渐把该删去的观念删净,他无法答对。你抽冷子问他今天天气好,他能把幼年上学忘带了书包也想起来。因此,他可是比别人想得精密,也不易忘记了事。早点去,老李。家常便饭,为是谈一谈。就说五点半吧? 张大哥不好命令到底,把末一句改为商问。好吧, 老李把事才听明白。 别多弄菜! 这句说得好似极端反对人家请他吃饭,虽然原意是要客气一些。老李确是喜欢有人请他去谈谈。把该说的话都细细预备了一番;他准知道张大哥要问他什么。只要他听明白了,或是看透言语中的暗示,他的思想是细腻的。整五点半,敲门。其实老李十分钟以前就到了,可是在胡同里转了两三个圈:他要是相信恪守时刻有益处,他便不但不来迟,也不早到,这才彻底。张大哥还没回来。张大嫂知道老李来吃饭,把他让进去。张大哥是不能够 不是不愿意 严守时刻的。一天遇上三个人情,两个放定,碰巧还陪着王太太或是李二婶去看嫁妆,守时间是不可能的。老李晓得这个,所以不怪张大哥。可是,对张大嫂说什么呢?没预备和她谈话!大嫂除了不是男人,一切全和大哥差不多。张大哥知道的,大嫂也知道。大哥是媒人,她便是副媒人。语气,连长像,都有点象张大哥,除了身量矮一些。有时候她看着象张大哥的姐姐,有时候象姑姑,及至她一说话,你才敢决定她是张太太。大嫂子的笑声比大哥的高着一个调门。大哥一抿嘴,大嫂的唇已张开;大哥出了声,她已把窗户纸震得直动。大嫂子没有阴阳眼,长得挺俏式,剪了发,过了一个月又留起来,因为脑后没小髻,心中觉着失去平衡。坐下,坐下,李老! 张大嫂称呼人永远和大哥一致。 大哥马上就回来。咱们回头吃羊肉锅子,我去切肉。这里有的是茶,瓜子,点心,你自己张罗自己,不客气。把大衣脱了。 她把客人的话也附带着说了,笑了两声,忽然止住,走出去。老李始终没找到一句适当的话,大嫂已经走出去。心里舒坦了些。把大衣脱下来,找了半天地方,结果搭在自己的胳臂上。坐下,没敢动大婶的点心,只拿起一个瓜子在手指间捻着玩。正是初冬天气,屋中已安好洋炉,可是还没生火,老李的手心出了汗。到朋友家去,他的汗比话来得方便的多。有时候因看朋友,他能够治好自己的伤风。以天气说,还没有吃火锅的必要。但是迎时吃穿是生活的一种趣味。张大哥对于羊肉火锅,打卤面,年糕,皮袍,风镜,放爆竹等等都要作个先知先觉。 趣味 是比 必要 更文明的。哪怕是刚有点觉得出的小风,虽然树叶还没很摆动,张大哥戴上了风镜。哪怕是天上有二尺来长一块无意义的灰云,张大哥放下手杖,换上小伞。张大哥的家中一切布置全与这吃 前期 火锅,与气象预告的小伞,相合。客厅里已摆上一盘木瓜。水仙已出了芽。张大哥是在冬腊月先赏自己晒的水仙,赶到新年再买些花窖熏开的龙爪与玉玲珑。留声机片,老李偷着翻了翻,都是新近出来的。不只是京戏,还有些有声电影的歌片 为小姐们预备的。应有尽有,补足了迎时当令。地上铺着地毯,椅子是老式硬木的 站着似乎比坐着舒服;可是谁也不敢说蓝地浅粉桃花的地毯,配上硬木雕花的椅子,是不古朴秀雅的。老李有点羡慕 几乎近于嫉妒 张大哥。因为羡慕张大哥,进而佩服张大嫂。她去切羊肉,是的,张大哥不用仆人;遇到家中事忙,他可以借用衙门里一个男仆。仆人不怕,而且有时候欢迎,瞎炸烟而实际不懂行的主人;干打雷不下雨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可是张大哥永远不瞎炸烟,而真懂行。他只要在街上走几步,得,连狐皮袍带小干虾米的价钱便全知道了;街上的空气好象会跟他说话似的。没有仆人能在张宅作长久了的。张大哥并非不公道,不体恤;正是因为公道体恤,仆人时时觉得应当跳回河或上回吊才合适。一切家事都是张大嫂的。她永远笑得那么响亮。老李不能不佩服她。可是,想了一会儿之后,他微微的摇头了。不对!这样的家庭是一种重担。只有张大哥 常识的结晶,活物价表 才能安心乐意担负这个,而后由担负中强寻出一点快乐,一点由擦桌子洗碗切羊肉而来的快乐,一点使女子地位低降得不值一斤羊肉钱的快乐。张大嫂可怜!张大哥回来了。手里拿着四个大小不等的纸包,腋下夹着个大包袱。不等放下这些,设法用左手和客人握手。他的握手法是另成一格:永远用左手,不直着与人交握,而是与人家的手成直角,象在人家的手心上诊一诊脉。老李没预备好去诊张大哥的手心,来回翻了翻手,然后,没办法,在裤子上擦了擦手心的汗。对不起,对不起!早来了吧?坐,坐下!我就是一天瞎忙,无事忙。坐下。有茶没有?老李忙着坐下,又忙着看碗里有茶没有,没说出什么来。张大哥接着说: 我去把东西交给她, 头向厨房那边点着。 就来;喝茶,别客气!张大哥比他多着点什么,老李想。什么呢?什么使张大哥这样快活?拿着纸包上厨房,这好象和 生命 , 真理 ,等等带着刺儿的字眼离得过远。纸包,瞎忙,厨房,都显着平庸老实,至好也不过和手纸,被子,一样的味道。可是,设若他自己要有机会到厨房去,他也许(不反对。火光,肉味,小猫喵喵的叫。也许这就是真理,就是生命。谁知道! 老李, 张大哥回来陪客人说话儿, 今儿个这点羊肉,你吃吧,敢保说好。连卤虾油都是北平能买得到的最好的。我就是吃一口,没别的毛病。我告诉你,老李,男子吃口得味的,女人穿件好衣裳,哈哈哈, 他把烟斗从墙上摘下来。墙上一溜挂着五个烟斗。张大哥不等旧的已经不能再用才买新的,而是使到半路就买个新的来;新旧替换着用,能多用些日子。张大哥不大喜欢完全新的东西,更不喜欢完全旧的。不堪再用的烟斗,当劈柴烧有味,换洋火人家不要,真使他想不出办法来。老李不知道随着主人笑好,还是不笑好;刚要张嘴,觉得不好意思,舐了舐嘴唇。他心里还预备着等张大哥审他,可是张大哥似乎在涮羊肉到肚内以前不谈身家大事。是的,张大哥以为政府要能在国历元旦请全国人民吃涮羊肉,哪怕是吃饺子呢,就用不着下命令禁用旧历。肚子饱了,再提婚事,有了这两样,天下没法不太平。六自火锅以至葱花没有一件东西不是带着喜气的。老李向来没吃过这么多这么舒服的饭。舒服,他这才佩服了张大哥生命观,肚子里有油水,生命才有意义。上帝造人把肚子放在中间,生命的中心。他的口腔已被羊肉汤 漂着一层油星和绿香菜叶,好象是一碗想象的,有诗意的,什么动植物合起来的天地精华 给冲得滑腻,言语就象要由滑车往下滚似的。张大哥的左眼完全闭上了,右眼看着老李发烧的两腮。张大嫂作菜,端茶,让客人,添汤,换筷子 老李吃高了兴,把筷子掉在地上两回 自己挑肥的吃,夸奖自己的手艺,同时并举。作得漂亮,吃得也漂亮。大家吃完,她马上就都搬运了走,好象长着好几只手,无影无形的替她收拾一切。设若她不是搬运着碟碗杯盘,老李几乎以为她是个女神仙。张大哥给老李一只吕宋烟,老李不晓得怎么办好;为透着客气,用嘴吸燃,而后在手指中夹着,专预备弹烟灰。张大哥点上烟斗,烟气与羊肉的余味在口中合成一种新味道,里边夹着点生命的笑意,仿佛是。老李, 张大哥叼着烟斗,由嘴的右角挤出这么两个字,与一些笑意,笑的纹缕走到鼻洼那溜儿便收住了。老李预备好了,嘴中的滑车已加了油。他的嘴唇动了。张大哥把刚收住的笑纹又放松,到了眼角的附近。老李的牙刚稍微与外面的空气接触,门外有人敲门,好似失了火的那么急。等等,老李,我去看一眼。不大一会儿,他带进一个青年妇人来。有什么事,坐下说,二妹妹! 张大哥命令着她,然后用烟斗指着老李, 这不是外人;说吧。妇人未曾说话,泪落得很流畅。张大哥一点不着急,可是装出着急的样子, 说话呀,二妹,你看!您的二兄弟呀, 抽了一口气, 叫巡警给拿去了!这可怎么好! 泪又是三串。为什么呢?苦水井姓张的,闹白喉,叫他给治 抽气, 治死了。他以为是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治的;反正是治错了。这可怎好,巡警要是枪毙他呢! 眼泪更加流畅。 还不至有那么大的罪过。 张大哥说。就是圈禁一年半载的,也受不了啊!家里没人没钱,叫我怎么好!老李看出来,她是个新媳妇,大概张大哥是媒人。果然,她一边哭,一边说: 您是媒人,我就仗着您啦;自然您是为好,才给我说这门子亲,得了,您作好就作到底吧!老李心里说, 依着她的辩证法,凡作媒人的还得附带立个收养所。张大哥更显着安坦了,好象早就承认了媒人的责任并不 止 于看姑娘上了花轿或汽车。 一切都有我呢,二妹,不用着急。 他向窗外叫, 我说,你这儿来!张大嫂正洗家伙,一边擦着胡萝卜似的手指,一边往屋里来,刚一开开门, 哟,二妹妹?坐下呀! 二妹妹一见大嫂子,眼睛又开了河。我说,给二妹弄点什么吃。 张大哥发了命令。 我吃不下去,大哥!我的心在嗓子眼里堵着呢,还吃? 二妹妹转向大嫂, 您瞧,大嫂子,您的二兄弟叫巡警给拿了去啦!哟! 张大嫂仿佛绝对没想到巡警可以把二兄弟拿去似的, 哟!这怎会说的!几儿拿去的?怎么拿去的?为什么拿去的?张大哥看出来,要是由着她们的性儿说,大概一夜也说不完。他发了话:二妹既是不吃,也就不必让了。二妹夫他怎么当上了医生,不是得警区考试及格吗?是呀!他托了个人情,就考上了。从他一挂牌,我就提心吊胆,怕出了蘑菇, 二妹妹虽是着急,可是没忘了北平的土话。 他不管什么病,永远下二两石膏,这是玩的吗?这回他一高兴,下了半斤石膏,横是下大发了。我常劝他,少下石膏,多用点金银花:您知道他的脾气,永远不听劝!可是石膏价钱便宜呀! 张大嫂下了个实际的判断。张大哥点了点头,不晓得是承认知道二兄弟的脾气,还是同意夫人的意见。他问, 他托谁来着?公安局的一位什么王八羔呀王伯高, 张大哥也认识此人。对了;在家里我们老叫他王八羔, 二妹妹也笑了,挤下不少眼泪来。好了,二妹,明天我天一亮就找王伯高去;有他,什么都好办。我这个媒人含忽不了! 张大哥给了二妹妹一句。能托人情考上医生,咱们就也能托人把他放出来。 那可就好了,我这先谢谢大哥大嫂子, 二妹妹的眼睛几乎完全干了。 可是,他出来以后还能行医不能呢?我要是劝着他别多下石膏,也许不至再惹出祸来!那是后话,以后再说。得了,您把事交给我吧;叫大嫂子给您弄点什么吃。哎!这我才有了主心骨!张大嫂知道,人一有了主心骨,就非吃点什么不可。 来吧,二妹妹,咱们上厨房说话儿去,就手弄点吃的。二妹妹的心放宽了,胃也觉出空虚来,就棍打腿的下了台阶: 那么,大哥就多分心吧,我和大嫂子说会子话去。 她没看老李,可是一定是向他说的: 您这儿坐着! 大嫂和二妹下了厨房。老李把话头忘了,心中想开了别的事:他不知是佩服张大哥好,还是恨他好。以热心帮助人说,张大哥确是有可取之处;以他的办法说,他确是可恨。在这种社会里,他继而一想,这种可恨的办法也许就是最好的。可是,这种敷衍目下的办法 虽然是善意的 似乎只能继续保持社会的黑暗,而使人人乐意生活在黑暗里;偶尔有点光明,人们还许都闭上眼,受不住呢!张大哥笑了, 老李,你看那个小媳妇?没出嫁的时候,真是个没嘴的葫芦,一句整话也说不出来;看现在,小梆子似的;刚出嫁不到一年,不到一年!到底结婚 他没往下说,似乎是把结婚的赞颂留给老李说。老李没言语,可是心里说, 马马虎虎当医生,杀人 都不值得一考虑?托人把他放出来张大哥看老李没出声,以为他是想自己的事呢, 老李,说吧!说什么?你自己的事,成天的皱着眉,那些事!没事! 老李觉得张大哥很讨厌。不过心中觉着难过 苦闷,用个新字儿。 大概在这种社会里,是个有点思想的就不能不苦闷;除了 啊 老李的脸红了。不用管我, 张大哥笑了,左眼闭成一道缝, 不过我也很明白些社会现象。可是话也得两说着:社会黑暗所以大家苦闷,也许是大家苦闷,社会才黑暗。老李不知道怎样好了。张大哥所谓的 社会现象 , 黑暗 , 苦闷 ,到底是什么意思?焉知他的 黑暗 不就是 连阴天 的意思呢 你的都是常 老李本来是这么想,不觉的说了出来;连头上都出了汗。不错,我的都是常识;可是离开常识,怎么活着?吃涮羊肉不用卤虾油,好吃?哈哈老李半天没说出什么来,心里想, 常识就是文化 皮肤那么厚的文化 的一些小毛孔。文化还不能仗着一两个小毛孔的作用而活着。一个患肺病的,就是多长些毛孔又有什么用呢?但是不便和张大哥说这个。他的宇宙就是这个院子,他的生命就是瞎热闹一回,热闹而没有任何意义。不过,他不是个坏人 一个黑暗里的小虫,可是不咬人。 想到这里,老李投降了。设若不和张大哥谈一谈,似乎对不起那么精致的一顿涮羊肉。常识是要紧的,他的心中笑了笑,吃完羊肉站起告辞,没有常识!不过,为敷衍常识而丢弃了真诚,也许 呕,张大哥等着我说话呢。可不是,张大哥吸着烟,眨巴着右眼,专等他说话呢。 我想, 老李看着膝上说, 苦闷并不是由婚姻不得意而来,而是这个婚姻制度根本要不得!张大哥的烟斗离开了嘴唇!老李仍然低着头说, 我不想解决婚姻问题,为什么在根本不当存在的东西上花费光阴呢?共产党! 张大哥笑着喊,心中确是不大得劲。在他的心中,共产之后便 共妻 , 共妻 便不要媒人;应当枪毙! 这不是共产, 老李还是慢慢的说,可是话语中增加了力量。 我并不想尝尝恋爱的滋味,我要追求的是点 诗意。家庭,社会,国家,世界,都是脚踏实地的,都没有诗意。大多数的妇女 已婚的未婚的都算在内 是平凡的,或者比男人们更平凡一些;我要 哪怕是看看呢,一个还未被实际给教坏了的女子,情热象一首诗,愉快象一些乐音,贞纯象个天使。我大概是有点疯狂,这点疯狂是,假如我能认识自己,不敢浪漫而愿有个梦想,看社会黑暗而希望马上太平,知道人生的宿命而想象一个永生的乐园,不许自己迷信而愿有些神秘,我的疯狂是这些个不好形容的东西组合成的;你或者以为这全是废话?很有趣,非常有趣! 张大哥看着头上的几圈蓝烟,练习着由烟色的深浅断定烟叶的好坏。 不过,诗也罢,神秘也罢,我们若是能由切近的事作起,也不妨先去作一些。神秘是顶有趣的,没事儿我还就是爱读个剑侠小说什么的,神秘!《火烧红莲寺》!可是,希望剑侠而不可得,还不如给 假如有富余钱的话 叫花子一毛钱。诗,我也懂一些,《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小时候就读过。可是诗没叫谁发过财,也没叫我聪明到哪儿去。不是实有其人,一点诗意!不管是什么吧。哼,据我看诗意也是妇女,妇女就是妇女;你还不能用八人大轿到女家去娶诗意。简单干脆的说,老李,你这么胡思乱想是危险的!你以为这很高超,其实是不硬气。怎说不硬气呢?有问题不想解决,半夜三更闹诗意玩,什么话!壮起气来,解决问题,事实顺了心,管保不再闹玄虚,而是追求 用您个新字眼 涮羊肉了。哈哈哈!你不是劝我离婚?当然不是! 张大哥的左眼也瞪圆了, 宁拆七座庙,不破一门婚,况且你已娶了好几年,一夜夫妻百日恩!离婚,什么话!那么,怎办呢?怎办?容易得很!回家把弟妹接来。她也许(0`x` t小`说 下`载`站www 。F v a L。cn)不是你理想中的人儿,可是她是你的夫人,一个真人,没有您那些《聊斋志异》!把她一接来便万事亨通? 老李钉了一板。不敢说万事亨通,反正比您这万事不通强得多! 张大哥真想给自己喝一声彩! 她有不懂得的地方呀,教导她。小脚啊,放。剪发不剪发似乎还不成什么问题。自己的夫人自己去教,比什么也有意味。结婚还不就是开学校,张大哥? 老李要笑,没笑出来。 哼,还就是开学校! 张大哥也来得不弱。 先把 她 放在一边。你不是还有两个小孩吗?小孩也需要教育!不爱理她呀,跟孩子们玩会儿,教他们几个字,人,山水,土田,也怪有意思!你爱你的孩子?张大哥攻到大本营,老李没话可讲,无论怎样不佩服对方的意见,他不敢说他不爱自己的小孩们。一见老李没言语,张大哥就热打铁,赶紧出了办法: 老李,你只须下乡走一遭,其余的全交给我啦!租房子,预备家具,全有我呢。你要是说不便多花钱,咱们有简便的办法:我先借给你点木器;万一她真不能改造呢,再把她送回去,我再把东西拉回来。决不会瞎花许多钱。我看,她决不能那么不堪造就,没有年青的妇女不愿和丈夫在一块的;她既来了,你说东她就不能说西。不过,为事情活便起见,先和她说好了,这是到北平来玩几天,几时有必要,就把她送回去。事要往长里看,话可得活说着。听你张大哥的,老李!我办婚事办多了,我准知道天下没有不可造就的妇女。况且,你有小孩,小孩就是活神仙,比你那点诗意还神妙的多。小孩的哭声都能使你听着痛快;家里有个病孩子也比老光棍的心里欢喜。你打算买什么?来,开个单子;钱,我先给垫上。老李知道张大哥的厉害:他自己要说应买什么,自然便是完全投降;设若不说话,张大哥明天就能硬给买一车东西来;他要是不收这一车东西,张大哥能亲自下乡把李太太接来。张大哥的热心是无限的,能力是无限的;只要吃了他的涮羊肉,他叫你娶一头黄牛,也得算着!老李急得直出汗,只能说: 我再想想!干吗 再 想想啊?早晚还不是这么回事! 老李从月亮上落在黑土道上!从诗意一降而为接家眷!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就以接家眷说吧,还有许多实际上的问题;可是把这些提出讨论分明是连 再想想 也取销了!可是从另一方面想,老李急得不能不从另一方面想了:生命也许就是这样,多一分经验便少一分幻想,以实际的愉快平衡实际的痛苦 小孩,是的,张大哥晓得痒痒肉在哪儿。老李确是有时候想摸一摸自己儿女的小手,亲一亲那滚热的脸蛋。小孩,小孩把女性的尊严给提高了。老李不言语,张大哥认为这是无条件的投降。设若老李在厨房里,他要命也不会投降。这并不是说厨房里不热闹。张大嫂和二妹妹把家常事说得异常复杂而有趣。丁二爷也在那里陪着二妹妹打扫残余的,不大精致的羊肉片。他是一言不发,可是吃得很英勇。丁二爷的地位很难规定。他不是仆人,可是当张家夫妇都出门的时候,他管看家与添火。在张大哥眼中,他是个 例外 一个男人,没家没业,在亲戚家住着!可是从张家的利益上看,丁二爷还是个少不得的人!既不愿用仆人,而夫妇又有时候不能不一齐出门,找个白吃饭而肯负责看家的人有事实上的必要。从丁二爷看呢,张大哥若是不收留他,也许他还能活着,不过不十分有把握,可也不十分忧虑这一层。丁二爷白吃张家,另有一些白吃他的 一些小黄鸟。他的小鸟无须到街上去溜,好象有点小米吃便很知足。在张家夫妇都出了门的时候,他提着它们 都在一个大笼子里 在院中溜弯儿。它们在鸟的世界中,大概也是些 例外 :秃尾巴的,烂眼边的,项上缺着一块毛的,破翅膀的,个个有点特色,而这些特色使它们只能在丁二爷手下得个地天天梦见天桥枪毙人,不敢出来。呕,在你那儿呢,那我就放心啦。 张大哥为客气起见,软和了许多;可是丁二在老李家帮什么忙呢?老李提着一笼破黄鸟走了。张大哥看着房契出神,怎回事呢?老李唯一值得活着的事是天天能遇到机会看一眼东屋那点 诗意 。他不能不承认他 是 迷住了,虽然他的理智强有力的管束着一切行动。既不敢 往好了说,是不肯 纯任感情的进攻,他只希望那位马先生回来,看她到底怎样办,那时候他或者可以决定他自己的态度。设若他不愿再欺哄自己的话,他实在是希翼着 马回来,和她吵了;老李便可以与她一同逃走。逃出这个臭家庭,逃出那个怪物衙门;一直逃到香浓色烈的南洋,赤裸裸的在赤道边上的丛林中酣睡,作着各种颜色的热梦!带着丁二爷。丁二爷天生来的宜于在热带懒散着。说真的,也确是得给丁二爷想主意 他一天到晚怕枪毙,不定哪天他会喝两盅酒到巡警局去自首!带他上哪儿?似乎只有南洋合适。他与她,带着个怕枪毙的丁二爷,在椰树下,何等的浪漫!小鸟儿,叫吧!你们一叫,就没人枪毙我了! 丁二爷又对着笼子低声的问卜呢!逃,逃,逃,老李心里跳着这一个字。逃,连小鸟儿也放开,叫它们也飞,飞,飞,一直飞过绿海,飞到有各色鹦鹉的林中,饮着有各色游鱼的溪水。他笑这个社会。小赵被杀会保全住不少人的饭碗,多么滑稽!正是个礼拜天,蝉由天亮就叫起来,早晨屋子里就到了八十七度,英和菱的头上胸前眼看着长一片一片的痱子。没有一点风,整个的北平象个闷炉子,城墙上很可以烤焦了烧饼。丁二爷的夏布衫无论如何也穿不住了;英和菱热得象急了的狗,捉着东西就咬。院子里的砖地起着些颤动的光波,花草全低了头,麻雀在墙根张着小嘴喘气,已有些发呆。没人想吃饭,卖冰的声音好象是天上降下的福音。老李连袜也不穿,一劲儿扑打蒲扇。只剩了苍蝇还活动,其余的都入了半死的状态。街上电车铃的响声象是催命的咒语,响得使人心焦。为自己,为别人,夏天顶好不去拜访亲友,特别是胖人。可是吴太太必须出来寻亲问友,好象只为给人家屋里增加些温度。老李赶紧穿袜子,找汗衫,胳臂肘上往下大股的流汗。方墩太太眼睛上的黑圈已退,可是腮上又加上了花彩,一大条伤痕被汗淹得并不上口,跟着一小队苍蝇。 李先生,我来给你道歉, 方墩的腮部自己弹动,为是惊走苍蝇。 我都明白了,小赵死后,事情都清楚了。我来道歉!还有一件事,我得告诉你。吴先生又找着事了。不是新换了市长吗,他托了个人情,进了教育局。他虽是军队出身,可是现在他很认识些个字了;近来还有人托他写扇面呢。好歹的混去吧,咱们还闲得起吗?老李为显着和气,问了句极不客气的, 那么你也不离婚了?方墩摇摇头, 哎,说着容易呀;吃谁去?我也想开了,左不是混吧,何必呢!你看, 她指着腮上的伤痕, 这是那个小老婆抓的!自然我也没饶了她,她不行;我把她的脸撕得紫里套青!跟吴先生讲和了,单跟这个小老婆干,看谁成,我不把她打跑了才怪!我走了,乘着早半天,还得再看一家儿呢。 她仿佛是练着寒暑不侵的工夫,专为利用暑天锻炼腿脚。老李把她送出去,心里说 有一个不离婚的了!刚脱了汗衫,擦着胸前的汗,邱太太到了;连她象纸板那样扁,头上也居然出着汗珠。不算十分热,不算, 她首先声明,以表示个性强。 李先生,我来问你点事,邱先生新弄的那个人儿在哪里住? 我不知道, 他的确不知道。你们男人都不说实话, 邱太太指着老李说,勉强的一笑。 告诉我不要紧。我也想开了,大家混吧,不必叫真了,不必。只要他闹得不太离格,我就不深究;这还不行?那么你也不离婚了? 老李把个 也 字说得很用力。 何必呢, 邱太太勉强的笑, 他是科员,我跟他一吵;不能吵,简直的不能吵,科员!你真不知道他那个 老李不知道。好啦,乘着早半天,我再到别处打听打听去。 她仿佛是正练着寒暑不侵的工夫,利用暑天锻炼着腿脚。老李把她送出去,心里说 又一个不离婚的! 他刚要转身进来,张大哥到了,拿着一大篮子水果。 给干女儿买了点果子来;天热得够瞧的! 随说随往院里走。丁二爷听见张大哥的语声,慌忙藏在里屋去出白毛汗。 我说老李, 张大哥擦着头上的汗, 到底那张房契和丁二是怎回事?我心里七上八下的不得劲,你看!老李明知道张大哥是怕这件事与小赵的死有关系,既舍不得房契,又怕闹出事来。他想了想,还是不便实话实说;大热的天,把张大哥吓晕过去才糟! 你自管放心吧,准保没事,我还能冤你?张大哥的左眼开闭了好几次,好象困乏了的老马。他还是不十分相信老李的话,可是也看出老李是决定不愿把真情告诉他: 老李,天真可是刚出来不久,别又老李明白张大哥;张大哥,方墩,邱太太,和 都怕一样事,怕打官司。他们极愿把家庭的丑恶用白粉刷抹上,敷衍一下,就是别打破了脸,使大家没面子。天真虽然出来,到底张大哥觉得这是个家庭的污点,白粉刷得越厚越好;由这事再引起别的事儿,叫大家都知道了,最难堪;张大哥没有力量再去抵挡一阵。你叫张大哥象老驴似的戴上 遮眼 ,去转十年二十年的磨,他甘心去转,叫他在大路上痛痛快快的跑几步,他必定要落泪。 大哥,你要是不放心的话,我给你拿着那张契纸,凡事都朝着我说,好不好?那 那倒也不必, 张大哥笑得很勉强, 老李你别多心!我是,是,小心点好!准保没错!丁二爷一半天就回去,你放心吧! 好,那么我回去了,还有人找我商议点婚事呢。明天见,老李。老李把张大哥送出去,热得要咬谁几口才好。丁二爷顶着一头白毛汗从里间逃出来: 李先生,我可不能回张家去呀!张大哥要是一盘问我,我非说了不可,非说了不可!我是那么说,好把他对付走;谁叫你回张家去? 老李觉得这样保护丁二爷是极有意义,又极没有意义,莫名其妙。三张大哥走了不到五分钟,进来一男一女,开开老李的屋门便往里走。老李刚又脱了袜子与汗衫。不动,不动! 那个男的看见老李四下找汗衫, 千万不要动!老李明白过来了,这是马老太太的儿子。他看着他们。屋门开了,马老太太进来: 快走,上咱们屋去! 妈! 马先生立起来,拉住老太太的手, 就在这儿吧,这儿还凉快些。马老太太的泪在眼里转, 这是李先生的屋子! 然后向老李, 李先生,不用计较他,他就是这么疯疯颠颠的。走!马先生很不愿意走,被马老太太给扯出来。丁二爷给提着皮箱。老李看见马少奶奶立在阶前,毒花花的太阳晒着她的脸,没有一点血色。大家谁也没吃午饭,只喝了些绿豆汤。老李把感情似乎都由汗中发泄出来,一声不出;一劲儿流汗。他的耳朵专听着东屋。东屋一声也没有;他佩服马婶,豪横!因为替她使劲,自己的汗越发川流不息。他想象得到她是多么难堪,可是依然一声不出。丁二爷以为马先生是小赵第二,非和李太太借棒槌去揍他不可,她也觉得他该揍,可是没敢把棒槌借给丁二爷。英偷偷的上东屋看马婶,门倒锁着呢,推不开;叫马婶,也不答应。英又急了一身的痱子。西屋里喀罗喀罗的成了小茶馆,高声的是马先生,低声的是老太太。西屋的会议开了两点多钟。最后,那个女的提起小竹筐,往外走。马先生并没往外送她。老太太上了东屋。东屋的门还倒锁着。 开开吧,别叫我着急了! 老太太说。屋门开了,老太太进去。老太太进了东屋,马先生溜达到北屋来。英与菱热得没办法,都睡了觉。三个大人都在堂屋坐着,静听东西屋的动静。马先生自己笑了笑。 你们得马上搬家呀,这儿住不了啦! 大家都没言语。啊! 马先生笑了。 都滚吧!李太太的真正乡下气上来了,好象是给耕牛拍苍蝇,给了马先生的笑脸一个嘴巴 就恨有俩媳妇的人! 好!很好! 丁二爷在一旁喝彩。马先生捂着脸,回头就走,似乎决定不反抗。李太太的施威,丁二爷的助威,马先生的惨败,都被老李看见了,可是他又似乎没看见。他的心没在这个上。他只想着东屋:她怎样了?马老太太和她说了什么?他觉不到天气的热了,心中颤着等看个水落石出。马先生的行为已经使他的心凉了些,原来浪漫的人也不过如此。浪漫的人是个以个人为宇宙中心的,可是马先生并没把自己浪漫到什么地方去,还是回到家来叫老母亲伤心,有什么意义?自然,浪漫本是随时的游戏,最好是只管享受片刻,不要结果,更不管结果。可是,老李不能想到一件无结果的事。结果要是使老母亲伤心,更不能干!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他的心已凉了一半:马少奶奶到西屋去吃饭!虽然没听见她说话,可是她确是和马家母子同桌吃的!到了夜晚,他的心完全凉了:马先生到东屋去睡觉!老李的世界变成了个破瓦盆,从半空中落下来,摔了个粉碎。 诗意 ?世界上并没有这么个东西,静美,独立,什么也没有了。生命只是妥协,敷衍,和理想完全相反的鬼混。别人还可以,她!她也是这样!起初,只听见马先生说话,她一声不出。后来,她慢慢的答应一两声。最后,一答一和的说起来。静寂。到夜间一点多钟 老李始终想不起去睡 两个人又说起来,先是低声的,渐渐的语声越来越高,最后,吵起来。老李高兴了些,吵,吵,妥协的结果 假如不是报应 必是吵!他希望她与他吵散了 老李好还有点机会。不大的工夫,他们又没声了。老李的希望完了,世界只剩了一团黑气,没有半点光亮。他不能再继续住在这里,这个院子与那个怪物衙门一样的无聊,没意义。他叫醒了丁二爷,把心中那些不十分清楚而确是美的乡间风景告诉了丁二爷。好,我跟你到乡下去,很好!在北平,早晚是枪毙了我! 丁二爷开始收拾东西。张大哥刚要上衙门,门外有人送来一车桌椅,还有副没上款的对联,和一封信。他到了衙门,同事们都兴奋得了不的,好象白天见了鬼: 老李这家伙是疯了,疯了!辞了职!辞! 这个决想不到的 辞 字贴在大家的口腔中,几乎使他们闭住了气。 已经走了。下乡了,奇怪! 张大哥出乎诚心的为老李难过。 太可惜了! 太可惜的当然是头等科员,不便于明说。 莫名其妙!难道是另有高就? 大家猜测着。不能,乡下还能给他预备着科员的职位?丁二也跟了他去。 张大哥贡献了一点新材料。 丁二是谁? 大家争着问。张大哥把丁二爷的历史详述了一遍。最后,他说: 丁二是个废物!不过老李太可惜了。可是,老李不久就得跑回来,你们看着吧!他还能忘了北平跟衙门?